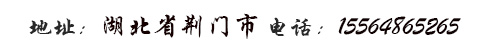这些年,我们见过许多被化名小娟的女孩
|
北京治白癜风要花多少钱 http://m.39.net/pf/a_4579158.html主持/方云槐剪辑/段思仪张潆予撰文/钟笑玫胡雅婷刘一萍 大多数时候,女性都是作为被动受害者,被人们看见她们遭暴力和不公碾过的狼狈模样。 站在三八妇女节,我们和三位最先看见或者记录小娟们的媒体人,试图与你一同回顾还原小娟们的遭遇,并告诉她们:你不是唯一的受害者,你也不是唯一的抗争者。《小娟(化名)》的字里行间 方云槐:大家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? 陈竹沁(《全现在》水瓶纪元作者):我最早想到的是合肥少女毁容案,当事人叫周岩。当时媒体报道的时候会写“这个十七岁少女拒绝官二代求爱,被烧伤毁容”。我那时还在读大学,性别意识也没有现在这么强,所以注意到的也是网民更多在谴责“官二代”这样一个身份。像《小娟》这样一首歌能够发表,还是能表明性别意识的进步。 黄霁洁(《澎湃新闻》人物栏目记者):《小娟》里面有句歌词,叫做“知晓我姓名,牢记我姓名。”它有点让我想到斯坦福大学性侵案,当时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,讲了一段受害者影响陈述。我感觉她公开自己姓名的行为,一定程度上是她不想以这个化名的身份作为一个符号、作为一个标签生活在这种社会新闻里面。她想让大家知道,她是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。 周建平(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编辑总监周建平):《小娟》里面有句歌词是一连串女字旁的字,“奻奸妖婊嫖姘娼妓奴……”,这些字的承受者是女性。歌词让我想到,我们的日常语言习惯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。遭家暴五十年方云槐: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,脑子里是柴静写的《看见》里面的一篇文章,叫做《沉默在尖叫》。讲的是一群被家暴的女人,她们最终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霁洁最近写了一篇一位女性杀害自己丈夫的报道:《困于家暴五十年:一起杀夫案始末》。你能讲一讲吗? 黄霁洁:我是去年十二月去采一个杀夫的案子。当时判决书里面写,她被家暴的时间有五十多年,直到某一天晚上,她趁丈夫熟睡的时候用擀面杖把他杀了。当时我非常想知道她是怎么在这五十多年里面生活下来的,因为这五十年几乎是她的一辈子了。 她和丈夫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,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,教育资源都给了自己的弟妹。她和丈夫有了感情以后就私奔出去,逃到另外一个村子里面。他们其实很早就结婚了,一开始,丈夫对她主要是暴力殴打,到了后面变得非常严重,是一种更强烈的控制,比如不允许她跟别的男人说话。这个过程中,她也做过挺多反抗,包括逃跑。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细节,她的村子旁边就是嫩江,这片江到了冬天会全部冰封,对岸是内蒙古的一个自治旗。 可以想象得出,那个时候她多么绝望。之后,丈夫还是骑摩托车把她给追回来了。这个案件本身就让我觉得触目惊心。方云槐:你刚刚说这个(家暴时间)跨度实际长达五十年。这五十年中她还生下了两个儿子,到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,他们现在的性格大概是怎么样的呢? 黄霁洁:案发的时候他们已经四十几岁了。去接触以后发现,他们对父亲还是挺恐惧的,晚上做梦还梦到父亲活过来,在那边闹,要打母亲。大儿子跟我说,他一直很想逃离这个家,就是不想在这个家里面待着,他整个心态都是非常麻木的。还有一个孩子对母亲非常依赖,所以他没有离开这个家。他妻子说他的口头禅是“没有用”,就是做啥都没有用。 即使他们的母亲最后以杀人的方式结束了这种家暴,但她还是挺痛苦的。因为她最后精神鉴定结果是“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”。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之后,不停地跟孩子说:“我其实没有想打死你爸,我就是想打残他,我养活他。”可以感觉到她一点也不想要杀人,但是她已经到了一种走投无路的地步。 方云槐:我想到一部美剧《致命女人》,这部剧带给一些观众一定的爽感,好像报复了一个渣男,但和你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,这件事情带给她的是一个悲剧,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。 黄霁洁:是的。她最后虽然脱离了家暴,但还是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。所以她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自由自在地做过什么事情。 方云槐:这个施暴者,也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人?你怎么去理解他的行为? 黄霁洁:他的妹妹说,他自己的父亲也有打母亲的行为。当时我想,他会不会也在经历一种暴力模式的的延续?这一类施暴者还挺典型的。我去采这个案子之前有看《冰点周刊》的另外一个报道,叫《一个遭遇家暴女人的致命还击》,里面的施暴者就是一个农村男性。当时他自己要建房子,但是他本身身体太瘦弱了,有肺气肿,这个房子就建不起来。 可是他们的家庭是完全不能负担的,会让我感觉有一部分的施暴者,可能是这样一个类型。 死于虐待、藏于阴婚方云槐:我们看到很多家庭暴力里面,施害者只有一个男人。但是有一起事件的主人公叫方洋洋,对她实施暴力的是她的婆家,也就是她的婆婆、公公和丈夫(详见文章《寂静的村庄:死于虐待,葬于阴婚》)。陈竹沁:我之前正好读了一个牛津学者HamsaRajan在青海藏族地区做的家暴田野调查,她分析了这种家庭结构带来的一个问题——婆媳之间的关系。 我们也能够想象,很多时候男性承担了比如外出打工(的责任),他不一定在这个家庭中。对于女性性别角色分工的规范,是由一个曾经从年轻媳妇成长起来的“婆婆”来承担的,所以“婆婆”更像是父权制的代言人。 放在方洋洋那个案子中也非常典型,它(的)事发地叫方庄,她嫁到的夫家叫张庄,之间也就隔了十公里。方洋洋在的方庄里,大家很少看到她,也就一年过年的时候看过她一次。当时村民已经见证了丈夫对她言语上、行为上恃强凌弱的感觉。也有村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冒犯,直接打了她的丈夫,可能也加剧了丈夫对于方洋洋,包括整个方庄的仇恨。 去张庄那边采访的时候,很多村民潜意识里也有一种自己是不是扮演了帮凶角色的愧疚感。但在面对记者质疑的时候,他们更多的是退避三舍,然后三缄其口。我当时也跟霁洁有一个同样想去求证的问题,就是方洋洋在长达半年的虐待过程中,她有没有反抗或者求助? 但我能够得到的,只是方庄的村民从张庄那边听过来的流言,说他的邻居曾经听到过方洋洋的哭声。也有一个说法,说她曾经逃跑过,方庄正好沿着一个铁路,她已经跑出去非常远,已经在玉米地里面。那个形象跟刚刚霁洁说她走在冰河上是一样的,非常有画面感。这个描述对我来说也挺有冲击的。 方云槐:听到这个故事,我有一个疑问:暴力会传染吗? 陈竹沁:在农村,婚嫁或者传宗接代的压力会把生育跟财产紧密地绑定在一起。对于方洋洋一家来说,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夫家的选择了。因为洋洋本身有一定心智障碍的问题,但即使是这样,夫家也要付出可能比其他女性相对少一些,但是也是十几万的彩礼。 所以当时张丙他们去方家去理论,也是说你要拿钱把这个病治好,就可以再继续生活下去。原先家庭没有承担这个之后,他们最终就采取了这种囚禁式的(方式),把她作为人质放在家里,宣泄自己的财物受到损失之后的一种发泄心理。 方云槐: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觉得方洋洋是一个很悲惨的人,她死得很悲惨,一生也过得很悲惨,但是她死后居然还要被拉去配阴婚,这个结局我一开始看到挺不能接受的。你当时是什么感受? 陈竹沁:我跟他们求证的时候,她叔叔和表哥来确认这个事情,他们还是带着一种比较朴素的农村观念,觉得我的责任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婚姻,有一个归宿。在你死后在地下,一个人就是很孤单,还是需要有一个男性的陪伴,也是对于家庭的一种传统的想象。被咬掉鼻子的女人周建平:跟刚刚两位老师的案例不大一样,我采访的时候见到当事人,她的反应异常平静。有可能因为她处于一个很安全的状态,她已经得到了公益机构的帮助,包括律师的,还有医疗的。有医院愿意帮她做鼻子的整形,也有一些公益机构愿意出钱帮助她的小孩继续接受教育,她的丈夫也在拘留所里面。但是对她女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,当时心理医生说,大女儿整个人非常木讷,你跟她搭话,她几乎没有反应。 方云槐:我对《被咬掉鼻子的女人:带俩女儿逃离家暴》另外一个印象还蛮深的细节就是,当这个施暴者的妻子提出要离婚的时候,他甚至会当着众人面前下跪,然后保证说再给我三个月,就这个样子,他好像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。你对于这个怎么看? 周建平:有些性犯罪相关专家说这种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,我觉得确实是这样。为什么对小孩很少存在这种循环?因为小孩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家庭或这个施暴者,而一个成年女性是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每次家暴之后,很多女性会说“我离开”或者“我要跟你离婚”,这种时候施暴者就通过道歉、下跪表现得非常真诚,其实是为了不让对方离开自己。 那种不寒而栗的爱情 方云槐:我发现另外一种暴力也越来越被大家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eiqizhongzl.com/fqzgb/1479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50个民间偏方,简单好学
- 下一篇文章: 哮喘会导致肺气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