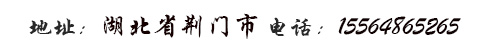童年往事01酒鬼
|
长沙哪儿有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yc/150505/4618893.html 童年往事 文/三清 01酒鬼 大伯爷爱喝酒在附近几个村是出了名的,他每天若没有几斤自酿的苞谷酒下肚,便会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 我们家很少去大伯爷家拜访,基本上每年只有拜年的时候才会去,但仅是拜年的那一顿饭,我也能窥见大伯爷的酒量。 大伯爷常年红着脖子红着脸,因为酒精的缘故,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。二伯和小舅劝着大伯爷注意身体,少喝点酒,他要么是不听,要么是一遍点头应着,一边嘴里喝着。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没有去年那么严格,拜年时我去了一趟大伯爷家。饭桌上我爸,我叔,我二伯,我小舅,几个大男人喝的找不着东南西北,一边喝一边胡扯。二伯哀叹小时候苦,长这大是怎么怎么不容易;我叔念着童年时的兄弟情,直说感觉人到中年,兄弟之间的情谊淡了,一年也见不着几次;小舅则谈起自己这几年过的不好,说着说着就差掉眼泪了;我爸则眯着眼,嘴咧着笑,时不时点头附和上几句。 几个人从艳阳高照喝到日暮西沉。按照习俗,晚饭后应该去给过世的亲人“送亮”,烧纸钱,让死去的亲人在地府也能过上一个好年。虽然每个人都喝了几斤酒下肚,但饭后他们还是开着车去了大伯爷的坟。 伯爷和伯婆没埋在一块,隔得挺远,具体原因不知道,但十有八九是村里的某个道士说了什么。开车从二伯家出发,走了二十分钟才到了伯爷土坟的地边儿。停了车,几个大人没管我们小孩子,我也就没去给伯爷烧纸。从小到大去伯爷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和伯爷话也没说过几句,真没啥感情。 大伯爷过世后,十里八乡的都说,大伯爷能活到八十多,命也算是好的了。村里像他那么喝酒的,根本没几个活得过七十。山里的酒基本都是自家酿的,度数高,酒劲大,我十一岁的时候喝过一口,喉咙辣了半天,吃完饭就昏昏沉沉的睡了。在喝酒这件事上,我及其敬佩他们这些老人。 “长大了就得喝酒,要不要来尝试一下白的?”大年初一的饭桌上,我爸,我叔,我姑爷,几个人又来劝我喝酒。我是一个平日及其冷酷的人,但面对这种局面,我只能笑着打哈哈。“我不喝酒,我不喜欢酒。”我说。 在我眼里,酒精的气味和味道是怪异的,闻着刺鼻,喝的烧喉,不知道有什么乐趣,可能他们喜欢喝醉之后的那种麻痹感吧! 历史上,刘伶、李白都被称为酒仙,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,一个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诗人。他们喝醉之后都能写出好诗,所以配得上“仙”的名号。我家里的长辈喝醉之后只能耍混说胡话,所以我私下里叫他们喝醉了酒的“鬼”,简称“酒鬼”。 老一辈喝酒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感情深一口闷”,每次聚餐都是一杯接一杯的灌,我常说,你们使劲喝,反正老了喝出病来,我才懒得管你们。这话进到平常人耳朵里,都会觉得是气话,但我说得久了,自己竟信了这真是我的内心想法。平日里感情寡淡,若真是喝酒喝出病,他们老了我可能真的不会管。 但“酒鬼”们也觉得我说的是气话,一切照旧,每次见面聚餐,还是离不开茅台五粮液梦之蓝,和苞谷酒。 对于喝酒这件事,我内心是非常抗拒的。但是这几年在家里宅久了,我也会乘着四下无人,在家里翻找藏在犄角旮旯的啤酒,有时是玻璃瓶装的青龙,有时是易拉罐装的青岛,逮住了就喝,喝完就瘫坐在椅子上望着对面的山,春天就数山上有几棵开了花的樱桃树,其他季节就看山顶上哪里又缺了一块“树皮”;或者喝完躺在自己窝里,看着天花板发呆,让脑子里的浆糊暂时沉淀下来。我享受那种晕晕乎乎的麻痹感,在晕着的几个小时里,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想,什么都不用管,就那么呆着,瘫着,像一个植物人一样。 “酒鬼”分三类。我叔是第一类,他每年为了工作全国上下到处组饭局,为了拿下客户或订单,遭了不少罪——至少在我看来,在这种饭局上喝酒是遭罪。但有时为了人际关系,喝的也十分尽兴;我爸这样的,是第二类,酒精对他们来说是打开心扉的钥匙。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样,人到中年,家庭、事业都稳定了下来,好像一眼就能望到埋进黄土里的那一刻,不能说一生碌碌无为,但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,值得旁人瞪大了眼看的大事。我爸虽说日子过得安稳,但有一个我这样的孽子,生活里也没有其他如意的地方,便觉得过往四十余年时光上蒙上了一层伤心的灰尘。遇到同样境地的人,便能续上一杯又一杯,一瓶又一瓶。我这样的,是第三类,一次不会喝多,喝到那种微微醉的状态最好。喝完酒啥也不干,只会沉浸在自己眼前虚无的幻境里,谁也摇不醒,谁也叫不应。刚开始喝酒只是因为一些奇怪的理由,有时是一时想不开,想醉死自己,有时是不想喝水,喝酒解渴。但最后也会慢慢的上瘾,爱上那种醉酒后的状态。 在我家族谱上,从我往上数三代,都有喝酒出了名的人才,但只有我是百年难得一遇的“奇才”——人前拒绝甚至鄙夷喝酒的行为,背地里却一个人喝得痛快。在亲戚家我从不喝酒,就算有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只在自家喝,拿着别人口中号称千杯不倒的啤酒,对着冷漠的墙品尝酒中的清香与苦涩。一瓶下肚,状态就来了。 但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。家中长辈喝醉后做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,平日里以沉闷乖宝宝形象示人的我,怎么可能让人看到我的“洋相”呢? 说到长辈们喝醉之后的有趣故事,那我是掰着两只手的手指头都数不过来。最早记得的一件事是在我爸的生日宴上。在十几年前,农村还兴摆酒席,大伙有针眼大点事都要摆上流水席,请上十里八乡有过人情的人去吃席,搞得大家的人情债是越来越多。我们家估计也是吃席吃怕了,我爸就决定,等他过生日的时候,也要摆上一道。 在老家,附近四五个村就一所小学,巧的是,我爸又刚好把周围熟人的孩子都教过一遍。到了办酒席那天,感觉几个村的人都挤到我们家了。虽然很多人都是还了人情就走了,但还是有不少来和我爸喝酒的。 我记得很清楚,我爸在院子边上那棵隔一年结一次果的李子树下专门摆了一桌,谁来找他喝酒他都接。那时我爸还没现在这么老气,学校的同事们也正是能喝的年纪。直径两米多的小饭桌上摆满了酒,白酒,啤酒,还有苞谷酒。我爸年轻时的酒量不行,旁边桌上吃席的人换了三轮他才喝醉,喝醉了就开始吹牛说胡话了,然后就是趴在桌上不醒人事。 吃到天黑,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,一伙人把我爸拖进了卧室,二伯给他端来一杯茶,他喝了没几口就哗哗吐了一地,一股带着酸味的恶臭在封闭的室内弥漫开来。我躲在卧室后门边闻到气味也差点吐出来。我爸看到门边靠着一个流着脏鼻涕的胖小孩,便招手让我过去,还一个劲地叫着我的名字。年少无知的我没见过这场面,撒腿就往外面跑,等跑到屋后的田坎上才停下来歇口气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拥有包含多种复杂情感的心情。 酒可不是个好东西,我以后一定不要喝酒。我想。 大伯爷去医院里度过的,那时他已经被严重的肝病和肺气肿折磨的不成样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去看他,在病房里,大伯爷让爸妈把病床摇起来,让他靠着说话。我则坐在一边的病床上观察着。听得出来,大伯爷很不好受,呼吸声犹如旧轮胎充气放气时的噗呲声。他每说一句话,就要长长地缓上一阵,吸一口氧。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能避之则避,但那一天,我就那样安静地坐在病床上,仔细地听着大人间的对话。 相比较同龄人,我似乎对周边的所有事都是漠不关心的态度。在我上学时的某一天,大伯爷去世了,然后在某个周末,和爸妈通话时他们告知了我这个消息。我随便应付的一句“哦”,便将那个悲伤的消息抛之脑后,就好像那个红脖子红脸的老“酒鬼”与我毫不相关。 但或许,我只是因为很久没有与他相见,将与他相关的记忆选择性遗忘了吧。现在,当我面对着白墙一个人喝酒时,一段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: 在去往给爷爷刻碑的碑场途中,那个满身酒气、红脖子红脸的慈祥老头,在路边给我买了一包鸡蛋面,让我中午别饿着。 真实故事,部分夸张 映小像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eiqizhongzl.com/jxfqz/1474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知白守ldquo乳rdquo,通
- 下一篇文章: 缘何我如此信任叶医生